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这似乎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法律能够定纷止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边界,是我们能够彼此大致相安无事地同处一个世界的可靠保证。但法律的价值是否仅止于此?事实上,法律不仅维系了秩序,还以自身独有的方式为之。它通过成文的规则与公开的司法判例表达了权力的掌控者或全体社会成员内心所期许的生活愿景。这种愿景一经法律明确,便具有了独立的生命,任何人都难以用任何方式违抗或藐视。
“我们需要法律来明确内心中的生活愿景,以便所有人都能对此愿景耳濡目染、感同身受,并且能够运用法律对此愿景的公开承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法律人类学教授费尔南达·皮里的新作《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的核心要义。秩序固然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秩序之外,法律也体现着人们更为宏大的生活愿景与理想信念。
秩序、愿景与信念
人类文明早期的法律中已经蕴含了秩序、愿景与信念这三个影响后来法律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三者的代表性文明分别是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教婆罗门的立法。在皮里的描述中,2000多年古代中国帝王的统治在强调惩罚与规训的同时,又不乏灵活色彩。比如,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总体维持着以刑罚为主的特征,历朝历代都希望通过刑罚制裁实现对社会各个层级的控制和监管。但在实际执行层面,法律的运作并没有其表面看来那样严格。皮里强调,古代中国的许多纠纷,特别是“民事”方面的,都是由地方宗族士绅、血亲长辈、甚至僧道调解结案的。统治者反而非常愿意展示出道德上的“人治”色彩,宣扬尊师重道、纲常伦理等儒家价值观。严密的刑罚制度与儒家“仁政”理念的互动,体现出古代中国的核心智慧。
相较于古代中国以刑罚为手段实现的秩序,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虽然同样强调成文立法与刑罚,但更为明显地表述了对于正义理念的追求。比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正义之王把人类子民交付给我招呼,啥玛什神把人类子民交给我带领,而我悉心关怀,不曾轻忽”。皮里指出,从历史材料分析,这部法典的内容不仅似乎从未真正付诸司法实践,而且即便得到严格执行,古巴比伦也会出现一种极其严厉的司法形式,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正义相去甚远。但皮里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这部法典中有关正义价值的阐述:它可能代表了当时社会成员对于正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因为在法典的结尾,汉谟拉比国王要求,法律应当对一位“富有洞察力,能够为他所统治的疆域提供公正的救济途径”的统治者有所启发。这一点得到了其他统治者的接受。这部法典的继续传播,最终在西方确立了以成文规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法律虽然是解决纠纷的工具,是国王实施权力的渠道,但同时也成为民众寻求正义的依靠。
法律在维系秩序、提出正义愿景之外,还体现着宇宙的秩序、反映着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皮里指出,在印度平原中宗教专家婆罗门依据《吠陀经》所阐发的法律,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印度教的传统中,法律和宗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法律规定除了包含日常行为规则,还涉及宗教献祭、血统纯洁等方面的内容。宗教专家同时也是法律权威,而法律由于源自宗教教义则不能由国王制定,只能由其颁布。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公元2世纪末出现的《摩奴法论》。这部法典的重点在于,个人应当根据其种姓、家庭和生活状况,做出正确的行为。相较于授予人们权利,它更侧重于规定人们的义务。依据这类“法论”(即法律和宗教规范),人们能够过上理想模式中纯洁的生活。
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教婆罗门的立法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传播与扩展。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古罗马的立法。在罗马人看来,法是由罗马公民制定的,是为罗马公民制定的,且承诺为所有人主持公道。同时,当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被居鲁士大帝摧毁时,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却延续下来,并逐步适应了犹太社会和伊斯兰社会,进而形成犹太教法和伊斯兰教法。
随着时间推移,进入中世纪后世界各地的法律秩序进一步变得精致和严密,规则形成的秩序往往与特定的宇宙观相关。这一时期的印度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法律秩序在提供秩序的同时,也赋予人们一种身份认同感,人们围绕宗教法律秩序建立起独特的习惯与制度,以应对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则不仅建立起世界上最无所不包、最法制化的行政体系,还将这种遵守法律的思想渗透到与来世的关系之中。比如,考古发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墓葬文献中包含着人们向神灵提交的诉状呈辞。此时的欧洲则经历了罗马法的重新发现,“法典化运动”在欧洲大陆方兴未艾,各国国王都愿意采用罗马法的形式来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律;英国也受此影响,开始展开对“不成文法”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普通法。
法律秩序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最终形成了如下生活方式:人们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一再诉诸法律并依靠客观规则所提供的确定感,法律由此成为约束权力行使或质疑统治者行为的根据。皮里指出,这意味着法治思想的雏形出现。在接下来现代社会中,这种思想伴随着欧洲法律的扩展而传向整个世界,逐步取代了与古代法律相连的宗教和宇宙观秩序。
法治的传播与殖民统治
在当今的世界中,法律与国家及其统治流程紧密相关。法律应当支持民主政体、实现高效监管、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并应当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解决纠纷。这一切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常识,可从历史角度分析,这种法律秩序从在欧洲大陆出现到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才二百余年的时间。在17世纪,欧洲各国的法律仍然是局部的、重叠的和杂乱的。但两方面力量推动了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出现。一方面力量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战。在持续的社会动荡中,人们开始更加务实地思考法律的目的及其可能实现的目标。许多人逐渐相信,人们不仅需要一种公正的法律体系,还需要一种能够超越统治者个人激情和敌意的法律体系,由此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活与生计。这种想法与当时另一方面的力量,也即法律的理性化需求结合了起来。在中世纪,大多数欧洲法院运用的都是各种规则混合而成的规制体系。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和方便,统治者要求人们汇总自己社群的规则,并建立了专业化的司法机构来实施这些规则。专业化的法律人才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立法向专业化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民众对于安定的需求,以及法律理性化的发展趋势,最终推动了英国普通法的统一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综合性法典的编纂。但这两股力量并非完全适配。民众需要法律安定,这不仅意味着法律应当具有理性和体系性,还意味着法律应当具有超越统治者意志的权威,否则法律只能构成统治者治理的工具。但是法律的理性化发展,往往源自统治者维护和扩展自身统治的需求。皮里认为,这两种需求之间的龃龉常常体现为现代早期人们有关自然法原则和成文法权威之间关系的论辩,抑或对于个人如何凭借自然权利免于统治者暴政的分析。近代早期的自然法学者,比如格劳秀斯、普芬多夫和洛克为自然权利学说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法律代表了一系列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且未经人民同意不得更改。
这种自然权利观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17世纪中叶之后的英国,已经逐渐将议会立法视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同时也坚持普通法的存在及其权威并不依赖于王权或议会,而是源自人们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欧洲大陆虽然法典化运动如火如荼,但法学家们试图建立的都是某种超越政治权威或政治分歧的法律形式。比如,当拿破仑作为查士丁尼的追随者,热切地认为统治者的意志应当构成法律时,当时的法律专家却并不认为他能够像上帝一样统治自己所创造的生灵,而是主张王权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统治者在此过程中自然会感受到法律的“掣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法律成为实施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
皮里敏锐地指出,欧洲殖民者当然并非首个将法律和政府体系强加给新领土和新人口的人。历史上的法律传播几乎都伴随着武力的征服,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新法与旧有的法律传统总是彼此共存,而非相互取代。但是,现代社会中的殖民统治使得欧洲的法律体系传播向全球,其广度和深度远非历史上任何一次法律移植能够比拟。同时,依赖训练有素的官僚政府以及高效的规训工具和监管手段的欧洲法律体系使得殖民地旧有制度迅速被边缘化。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北美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哄骗原住民签下了后者并不理解的合同,以包括运用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占取了原住民手中的土地。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情况变得更糟。新创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及其州政府奉行激进的土地政策,以缔结“条约”的名义强行无偿没收原住民的土地。他们在表面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却向原住民赊销商品并要求其以土地偿还。最终,在1823年著名的约翰逊诉麦金什案中,法官判定原住民只是“占有”土地而不拥有其“产权”。由此可见,法律被用作实现“落后”地区“进步”的统治手段,成为殖民活动的掩护。
在殖民活动之外,法治理念也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传播。皮里指出,在20世纪世界各地的新兴国家和后殖民政权都可以仿效欧洲的法律模式,甚至没有经过殖民统治的国家也会如此。这种现象可能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一股力量是欧洲殖民者通过殖民活动,将自己的社会与政治理念引入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观念持续塑造着后殖民时代的各国秩序。另一股力量则是欧洲法律秩序中所蕴含的有关文明、进步和国际秩序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确立,即使未经过殖民的新兴国家也意识到只有仿效欧洲的法律体系才能够更容易参与新的经济和商业秩序。至此,欧洲法律体系在现代世界获得了极强的支配地位。
法律多元主义
但欧洲法律秩序取得的胜利恐怕只是表面上的。皮里敏锐地发现,从19世纪末直到今天,欧洲法律体系并没有完全取代或清除世界各地自身的法律传统。这些法律传统虽然在历史发展中被逐步贬斥为“落后”与“守旧”,成为一次又一次革新的对象,并且不再得到各自官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却一直发挥着指引人们行为、规划人们生活、判定是非对错的作用。在法律人类学的分析中,这便是经典的法律多元现象。它意味着在同一片土地上存在两个或以上同时生效的法律体系,且彼此之间在效力层级方面难分轩轾。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甚至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自身。
前者典型的例证就是伊斯兰教法的实施。皮里发现,尽管伊斯兰教法并未得到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正式承认,但却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非常受欢迎。皮里认为,伊斯兰教法不仅是与伊斯兰国家官方法律体系并行的法律,还是一种与现代国家截然不同的秩序观。后者的典型例证则出现在美国和意大利。比如,法律人类学家莎利·法尔克·穆尔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纽约的时装从业者会通过生产和零售网络规避美国联邦批准的工会条例的规制。服装产业具有非常强的季节性,短时间内可能会对特定商品有非常巨大的需求,但一段时间过后,可能这些产品便无人问津。当时的服装由时装屋设计和生产,它们将制造服装的工作交给分包商,后者则拥有车间并雇佣女工完成订单。服装产业的季节性往往会使得短期内分包商需要完成大量衣服的制作,女工就需要加班加点完成订单,而这种行为明显超出了工会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工会的业务代理人会与分包商的车间经理对接,并定期走访车间,以确保工人获得适当的工资以及适当的工作时长。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工会的业务代理人当然了解服装产业的经营特性,车间经理也希望他们不会严格执行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为此,车间经理就会同工会代理人搞好个人关系,比如,赠送礼物,特别是定制衣服,以此换得工会代理人的“通情达理”。
同样典型的还有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它起源于19世纪初,一开始是保护企业免受匪患侵害的暴力团体,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组织。黑手党在社会中发挥着提供保护、执行协议和调解争端的作用,但他们并不依靠法律来行使权力,而是从合法和非法的商业中攫取资源,并依靠声望以及暴力有效地管理着各种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皮里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并不单纯依靠法律。但她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没有价值。恰恰相反,这些国家法之外的秩序在双重意义上体现出法律的可贵。首先,在国家法之外的秩序中有一些也体现出了法律的精神或内涵。比如,宗教的信徒、草原上的牧民、乡村中远离国家法律的村民以及特定商业中的从业人员,他们可能为了有效规范和控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会制定出类似于法律的规则,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事物。其次,国家法之外的秩序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成文法律的价值。国家法之外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成文的,进而也是模糊和有弹性的,有可能受到个人意志的改变或废弃,这就便利了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控制和压迫他人。换言之,国家法之外的秩序,特别是像黑手党规则这样的秩序从反面表明,成文规则不仅是实施统治的有效工具,也是限制权力的有效依据。
因此,皮里主张法律本身并无善恶倾向。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当然不乏带有追求私利、玩弄权术的色彩。但重要的是,当一个命令成为公开的规则进而被宣告为法律后,人们就可以援引、依赖或使用它来反对腐败和规则的滥用。这似乎意味着皮里认为,尽管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仅由法律实现,但相较于其他实现社会秩序的手段,法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简言之,法律之外的规范体系尽管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可能都由于缺乏法律的公开性与成文化的特征而难以长久维系社会秩序。这进一步隐含着如下推论,即随着人类社会演进,众多行为规范在逐渐发展成熟后,要么会演变为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律,要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皮里的论述其实隐含着一个不同于法律人类学主流立场的判断:法律多元现象无论涵盖范围多么广泛,持续时间多么长久,它可能都是一种暂时或过渡的状态;国家法最终会构成人类社会唯一根本的法律形态。
法治的多元路径
皮里的判断在法律人类学领域中可能并不算主流,但在法学理论的语境中,这种国家法一元论的立场颇为盛行。这种观点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当代法律多元主义与法治理论重要的倡导者布莱恩·Z.塔玛纳哈指出,法律的多元样态可能实际上更有助于实现法治的本质功能。这是因为一如皮里所言,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欧洲法律体系为模板,通过法律移植等方式确立了本国法律制度。但是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官方正式确立的法律由于一系列原因而运转失灵,比如缺乏足够的律师和法官,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及缺乏法律体系能够良好运作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从这个角度思考,反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有的规范体系能够更好地发挥指引人们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家法未必是实现法治的有效途径,甚至国家法本身的运作都建立在其他类型的规范甚至法律体系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皮里的主张是相当脆弱的。当她将实现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制定且公开颁行的成文法律时,她其实忽略了当抽空其他类型的社会规范而只留下国家法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可能反而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处理日常的纠纷,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就会受到实质性减损。当然,皮里的关切是:只有规则得到明确的表述而成为法律后,受其规制的人们才能够运用法律保护自己,法律由此不仅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权利的保护。但这同样忽略了在国家法之外的法律形态或规则体系中,人们运用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缝隙或规则本身包含的操作空间来规避不合理的规则、反对不合理的要求并保护个人的正当权益。规则会为人们提供保护,但逃避规则同样也会。
此外,皮里自己的举例其实也难以支撑她的主张。无论是她对伊斯兰教法的刻画,还是对于意大利黑手党、美国纽约时装行业惯例的分析,其实都表明明面的成文规则由于具有“刚性”而难以掌控流变不居的社会:国家法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自然是重要的,但难以说是最重要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法律的运作不仅依赖于制度、程序、人员配备,也依赖于民众的了解和熟知。国家自然可以凭借其权威设立众多法律规范,但在日常生活中民众的行为举止却更多地依赖习以为常的惯例、成规和心照不宣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皮里勾勒的法律秩序四千年演变,在表明国家背书的成文规则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表明法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国家法与其他法律类型彼此配合。□赵英男
当代法律多元主义与法治理论重要的倡导者布莱恩·Z.塔玛纳哈指出,法律的多元样态可能实际上更有助于实现法治的本质功能。这是因为一如皮里所言,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欧洲法律体系为模板,通过法律移植等方式确立了本国法律制度。但是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官方正式确立的法律由于一系列原因而运转失灵,比如缺乏足够的律师和法官,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及缺乏法律体系能够良好运作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从这个角度思考,反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有的规范体系能够更好地发挥指引人们行为的作用。
转载请注明来自食非遗_游非遗_寻非遗,本文标题:《在秩序之外,法律还可以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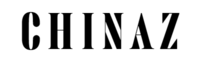












 京ICP备16068391号
京ICP备1606839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